2014年11月26日14:43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泽贤 点击: 次
——写在《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面世之际
在“文革”中,巴金被称作“黑老K”受到批判,曾有一段时间(记得已是“文革”后期)他被拘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6号楼,与我居住的宿舍仅相隔几个门洞。每天一早或傍晚,都能看到他独自一人拎着两只热水瓶去打水,看管并不是很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正好在打水,巴金就在身旁,彼此打量了片刻,沉默相对,便离开了。第二次碰面时,我“斗胆”问道:“你每天都来打水?”他打量了我一下,毫不经意地答道:“打水,是散步……”见有人过来,他便拎起水瓶匆匆地走了。以后又多次在打水的地方碰到他,都碍于当时的情势,不便多问,每天只好在宿舍窗口望着他从小路慢慢地走过去又走过来……
历史,在某一瞬间,往往会非常奇怪地定格:一个名人与一个普通人擦肩而过,我认识他,他却对我一无所知……
我认识他,是从他的著作,从“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到“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从《神•鬼•人》到《龙•虎•狗》;从《憩园》到《寒夜》;从《丹东之死》到《草原故事》……他的著作几乎全部翻阅过,虽未全部读完读通,且读过之后并不是全部都喜欢,或者说还不能构建起对他著作内容的偏爱。但我更爱他的著作版本,这虽是一种形态,却是渗透着丰富内容的外在形态。我是从建国之后的版本开始搜寻,一直延伸到建国之前的旧版本,在逐渐向后延伸的过程中重新阅读和体悟,居然感受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阵阵颤动和豁然开朗,巴金的清晰面貌从他的著作版本中逐渐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对他的偏爱,是从他那众人皆知的沉默寡言,到内心隐藏着的烈焰般激情,到坦诚相见开诚布公的流露,到隐与显同时并存的强烈个性,一直偏爱到他那包括所有情感的著作版本……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巴金无疑是一位巨人,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巨人不少,但他是个有别于其他巨人的巨人:沉默与激情和谐糅合的巨人——那是一种何等的跨度和力度啊!
巴金一生能体现高尚精神境界和完美人格力量的财富,如果以单本著作罗列的话,那是很长一串的排列,现在这些单本著作已经汇集在了二十六卷本不朽著作和十卷本精彩译著之中,读者完全可以从容地一页一页地阅读。然而研究者或爱好者往往忽略了一个巴金一生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他所主编或参与,他所关心或过问的现代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这也是我从偏爱到真爱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个著作等身,而且超越了自我,把自己的爱与激情奉献给他人,为他人作嫁衣裳,有时还要在误会与责难之中行进,虽也时有难言或委屈,但他始终没有停步,没有退缩,没有气馁。他把对作者的爱放在了心灵的深处,其他的一切皆可抛弃:这就是巨人啊,一个有别于其他巨人的巨人!我是从巴金所著的一本本著作版本“点滴”式的认识开始,直到从他所主编或编辑的一套套现代文学丛书才最终“全面”认识他的,这可以说是对一个既有丰厚著作铺垫,又有广阔丛书扩展的作家的一次全面认识。
在这种认识中,我牢记住了他的不少朴实得如同大白话的至理名言,这是他在主编或编辑丛书时的另一笔可贵财富,这些话原载于《巴金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朋友们试办出版社,约我参加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就答应下来。
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
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我并不怕失业,因为这是义务劳动。不过能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好,有关一个人的信用。搞好与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的项目之一,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我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我觉得惭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负责编辑、看过校样的书稿印出来后错字不少,越是后期出的书,错字越多。对作者和对读者我都感到歉意。
读了这些话,会使一个想干点事的人流泪,更会想起巴金在《随想录•大镜子》中说过的一句话:“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
关于“留下一点东西”,巴金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除此,他还为他人“留下一点东西”,更是做得“惊天动地”!我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当你站在这一套套的丛书面前,不由自主地会感受到一种由惊讶、困惑、钦佩直至震撼的感觉——这就是巴金留给我们的“一点东西”——使读的人心里锃亮,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暗淡”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如今,我把自己收藏和闻见的,巴金主编或编辑,关心或过问的部分现代文学丛书奉献给诸位,让我们捧着他的“精神财富”,一起忘掉所有讲好话的悼词,以他自己的“一点东西”,让自己永生!
本文系作者为《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1935-1949》(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所撰《自序》。标题系编者所加。
《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选刊)
《锦帆集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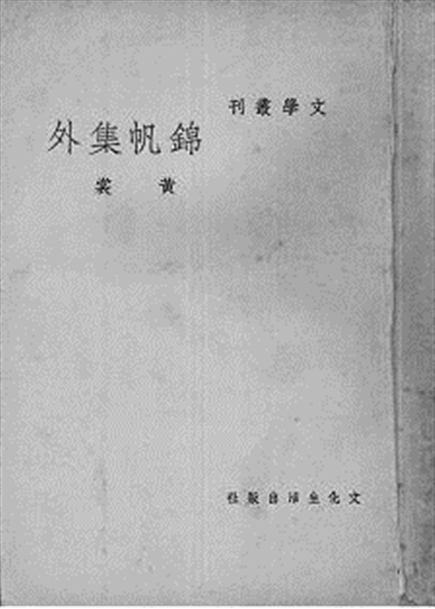

“文学丛刊”第九集,散文集,巴金主编,黄裳著,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平装初版,定价八元六角,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发行人吴文林,文化生活印刷所印刷。版权页左侧有第九集十六种书目。
全书253页,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江上杂记(一、二、残篇)、茶馆、桂林杂记、贵阳杂记(一、二、三、四、五)、昆明杂记(一、二、三、四、五、附记一、附记二),第二部分:凤、海上书简、跋“卖艺人家”、旅京随笔、鸡鸣寺、关于“泽存书库”、“美人肝”),第三部分: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风尘、李林先生纪念、更谈周作人、老虎桥边看“知堂”。书末两篇谈周作人的文字,颇具史料价值,也相当有趣。
作者的《后记》1947年除夕写于上海,其中说道:
这里收集了我近两年间胡乱写下来的文章的一部分。结集的时候在今年夏天,找寻出版的地方颇感到了困难。终于还是交给了PK先生。我的第一本集子《锦帆集》也是由他介绍出版的,这本集外就又麻烦了他,在这个烽火满天万方多难的时代,能看到这一本稿子寄出发排,我心里是充满了衷诚的欢喜与感谢的……至于还有一些杂文,将来想另编一集,不附此卷之末。
这里所指“PK先生”,即巴金,这是他众多笔名中的一个。据研究者分析,“PK”最早见于译文《母亲的死》(俄国赫尔岑著,载于1929年2月15日《自由月刊》一卷二期)。巴金用字母作为笔名者,除“PK”外,还有LiFei-kan、BaKin、B.B.等。
黄裳的《锦帆集》,是由中华书局初版于1946年11月,属“中华文艺丛刊”之一。《后记》中讲到是由巴金介绍出版的,其实巴金正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委员之一,在丛书书前印有以姓氏笔画为序的“中华文艺丛刊编辑委员”名单,除巴金外,还有柳无忌、朱自清、茅盾、孙伏园、宋云彬、靳以、金兆梓、叶圣陶、洪深。
《快乐王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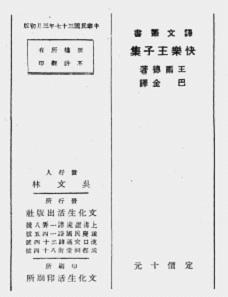
“译文丛书”,王尔德选集,童话散文集,王尔德著,巴金译,民国三十七年三月(1948年3月)初版,定价十元。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发行人吴文林,文化生活印刷所印刷。
书前有王尔德肖像,法国Heinrich Vogeler-Worpswede作插图。
全书225页,收童话九篇:少年国王、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渔人和他的灵魂、星孩、快乐王子、夜莺与蔷薇、自私的巨人、忠实的朋友、了不起的火箭。收散文七篇:艺术家、行善者、弟子、先生、裁判所、智慧的教师、讲故事的人。
书末有巴金写于1947年11月的《后记》,四页,其中说道:
二十年前我起过翻译英国诗人奥斯加•王尔德的童话(或译仙话)的念头。可是我始终不敢动笔。他那美丽完整的文体,尤其是他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他有着丰丽的辞藻,而我自己用的字汇却是多么贫弱。
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却开始做起这种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来……
单从这一册童话和散文诗集看来,我们也可知道王尔德一生所爱的东西只有两样:美与人类……
《小人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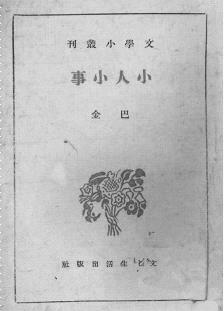

“文学小丛刊”第三集,短篇小说、散文集,巴金编辑并著,民国三十二年四月(1943年4月)初版,民国三十二年六月(1943年6月)蓉一版,此书为蓉一版,定价国币九元五角,文化生活出版社(成都陕西街138号,重庆民国路21号,桂林中北路桂北商场)发行,发行人吴文林。
笔者在此全录文化生活出版社当时的地点,并非累赘,从中可以窥探出种种变化,比如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民国路28号“变”为“21号”,变化只是表相,可惜对背后的故事知之甚少。
全书108页,分两辑,第一辑旅途通讯:别桂林及其他、“贵阳短简”及其他、成渝道上;第二辑小人小事: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
书末有巴金写于1942年11月的《后记》:
今年三月起我从桂林到重庆、成都,又从成都、重庆回到桂林,整整花了七个月的长时间。这期间内我只写了前面三篇通讯和三篇类似小说的东西。算字数,至多也不过三万八九千,而且是在几个地方写成的。这一叠原稿纸跟着我跑了来回将近三千公里的路程。到今天我拿出它们翻看,在这些纸上我仿佛封闭着公路上尘土的气息,这气息对我已经是非常亲切的了。我现在很高兴地把它们编成一本小书,作为我这次旅行的一个纪念物。
本来我想在“小人小事”的题目下写十篇像《猪与鸡》的文章,但只写了三篇就不想写了。所谓“小人小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说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一些渺小的事而已。“旅途通讯”三篇所写的也无非“小人小事”:我自己原是一个渺小的人。因此我就用了“小人小事”做这小书的题名。
194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以“文学丛刊”之名出版了《小人小事》,并称初版(1947年8月还出了再版),实际真正的初版应是1943年4月版,但这个版本笔者至今未见,见到的只是蓉一版。“文学丛刊”版与“文学小丛刊”版都有《后记》,两者虽有差别,但意思并没有变,稍作增删而已。有所改变的是“文学丛刊”删去了三篇通讯,只留短篇小说,成了一本纯粹的小说集。
《何为》



“新译文丛刊”,俄国切尔勒雪夫斯基著,罗淑译,平明出版社(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号)1950年3月初版,1953年3月三版,此书为三版。初版印三千五百册,到三版时已印六千五百册,每册定价人民币六千一百元。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经售。在版权页下方,还印有“定价页192”和“文学•艺术”。
书中有插图八幅。书前有《编者序》和《自序》。
《编者序》未标明,一页,写于1950年2月6日,应该是巴金的手笔:
这本《何为》是从薇拉•司塔尔科瓦的法文节译本转译的。俄文原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节译本虽只是一个概要,但作为一个中篇小说,或较长的短篇小说看,它也是一件不坏的艺术品。
译者罗淑是一个留法的女作家,《何为》节译本是她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里译出的,曾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过两千册,但也已经绝版多年了。最近编者偶然在旧书堆中翻出译者的手稿,觉得还有重印的价值,便把它交给平明出版社负责人拿去重排。
关于切尔勒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也是罗淑的译文,《何为》初版本中没有收入,记不起来是为了什么缘故。现在编者把它放在新版的卷首,让它第一次跟读者见面。
译者罗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成都病故。过些天便是她的逝世十二周年纪念日。她在这人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四年,可是她已留下了一些不能被时间磨灭的纪念。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在想念她。那么这本小书就作为供在她的灵前的祭品吧。
《自序》可能就是编者称的“关于切尔勒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未署名。开头第一句是:“我的善良的公众!这小说的主要价值就在它的真实。”
书末有巴金写于1936年4月的《后记》,正文加注共九页,在介绍“文化生活丛刊”的《何为》时,笔者曾摘录了其中的几段,读者可能参见,在此不再赘述。最后还有两段可以留存:
切尔勒雪夫斯基的《何为》就是在这时期(一八六三年)出现的,他把握住了这个现实,由此创造了新妇女的典型,表现了当时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们应该有的观念,应该走的道路。
这是七十几年前的旧作了。然而这,这道路在现今仍还是很新的。所以这本小书的翻译,虽无接受文学遗产的意义,却也自有其独特的使命的。